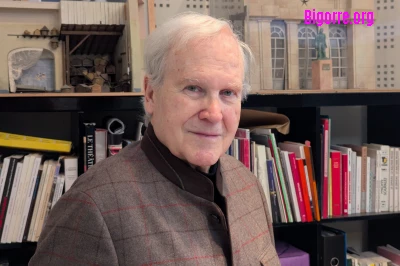你是如何成为如今的文化人的?
战后年代,我生长在乡下,一无所有。书籍、娱乐,我都只是从母亲那里听说的。她对娱乐这件事情有些怀旧,也有些浪漫,她告诉我一些我从未亲眼见过的事情。学校是我唯一能让我感到满足的地方,而我之所以要说那些平庸的老师,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乡巴佬。总的来说,我没有像加缪那样与他的老师相遇。我努力在黑暗的夜里前行。祖母带我去看路边喜剧演员的表演,他们穿梭于乡间。在那里,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表演艺术的刺激,面对着那些或许毫无艺术趣味却又在我心中燃起火花的东西。天空下发生了一些事情,打破了你每天被困的日常琐事。
那时离文化还很远!
另一个重要因素: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在寄宿家庭度过的。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彻底的脱离。它既彻底又有益,因为它切断了我与周围环境的联系,正如布迪厄所说。我受了很多苦,也感到无聊。无聊的时候,你就会读书。我像自学者一样读书:什么都读。塞涅卡和博须埃的《布道》,蒙田和克劳德·法雷尔。然后我很快就发现了一些东西。我手里拿着博须埃的布道文四处走动,讲解它们,看看效果如何。突然间,老师们,甚至有些老师,都在好奇这是什么鸟?突然间,我想起了我的戏剧经历,并对自己说:“你必须有创意,你必须有自己的东西。你必须有所培养。”正是这两个因素塑造了我的学习方法。所有这些都在我大三的时候汇聚在一起。我加入了一个由哲学老师领导的剧团。在那里,我发现了戏剧的乐趣、表演的乐趣、学习诗歌的乐趣。我和一位哲学老师的友谊,也决定了我的方向,因为我后来成为了一名哲学老师。我渴望文化,也渴望哲学和戏剧这两个极端。这后来成了我的一个难题。
你更愿意成为戏剧导演而不是演员,还是继续做哲学老师?
你成就了一番事业,却不知道为什么。但你是想从事戏剧事业,还是哲学事业?在我的学生时代,我一直处于纠结之中,以至于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安东尼·阿尔托的论文,他让戏剧变得不可能。我花了三年时间研究安东尼·阿尔托的失败,这正是我想要的失败,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气跳入虚空,成为一名演员或导演。我见识过很多东西,包括谢罗,以及我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其他人。我觉得如果我没有达到那个水平,那就不值得了。文化界有创造者,也有传承者。一位老师,一位文化人。文化传承下来的人有责任去传承。两者都不可或缺。画家需要画廊,作家需要出版作品。我体验到了我们在娱乐界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。
您创办巴黎文化中心(Parvis)的初衷是什么?
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文化之家(Maisons de la Culture)。我克服了没有这样一家机构来做我最爱的事情的失望。我以企业家的心态去做了这件事。企业家是那些愿意为了自己的想法冒一切风险的人。那是在1968年5月。你必须走出剧院,去发明创造,走进大自然,走进工厂,去寻找非公众的东西。当时我是一位哲学教授,同时也是一位戏剧爱好者,但生活并不安定。我娶了一个勒克莱尔经销商家庭的妻子。他们聊起了超市和分销业务。我发现这很有效,这些地方人潮涌动。这里的人形形色色,仿佛是对传统市场社交生活的某种重塑。这些人就在那里,那些我们试图用文化触达的名人。
这事儿非做不可!
我不会放弃。我向这些家庭成员、银行家和开发商们提出了一个项目。我很幸运,遇到了一位水平更高的银行家,他同意了,我们来融资,让我们做个项目吧。光说喜欢戏剧、喜欢哲学是不够的。我发现,像艾美酒店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总成本中,可利用的面积占了很大一部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