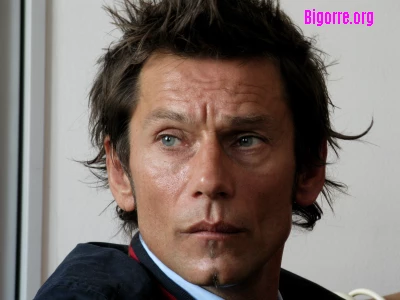дјҠиҺҺиҙқе°”В·дәҺдҪ©е°”дё»жј”зҡ„гҖҠиҸІеҫ·жӢүгҖӢеңЁе·ҙй»ҺеҘҘеҫ·зҝҒеү§йҷўйҰ–жҳ еҗҺеҮ еӨ©пјҢе…Ӣж—Ҙд»ҖжүҳеӨ«В·з“ҰйҮҢ科еӨ«ж–Ҝеҹәе°ҶдәҺдёӢе‘ЁдәҢе’Ңе‘Ёдёүдёәжі•еӣҪеҸҰдёҖз«Ҝзҡ„и§Ӯдј—еёҰжқҘдёҖеңәе Әз§°жң¬еӯЈжҲҸеү§зӣӣдәӢзҡ„жј”еҮәгҖӮиҝҷдҪҚжӣҫжӢ…д»»еҪјеҫ—В·еёғйІҒе…ӢеҠ©жүӢзҡ„жіўе…°еҜјжј”пјҢеңЁж¬§жҙІжҲҸеү§з•Ңдә«жңүзӣӣиӘүпјҢд»–йҖҡиҝҮиҝҷйғЁгҖҠжі•еӣҪдәәгҖӢеёҰйўҶжҲ‘们иө°иҝӣж–ҮеҢ–зҡ„ж·ұеӨ„пјҢйўҶз•Ҙ马еЎһе°”В·жҷ®йІҒж–Ҝзү№зҡ„гҖҠиҝҪеҝҶдјјж°ҙе№ҙеҚҺгҖӢгҖӮж”№зј–иҝҷйғЁе·ІжҲҗдёәжі•еӣҪж–ҮеӯҰдё°зў‘зҡ„дјҳзҫҺдҪңе“ҒпјҢж— и®әеӨҡд№ҲиҮӘз”ұпјҢйғҪжһҒе…·жҢ‘жҲҳжҖ§пјҒзәҰз‘ҹеӨ«В·жҙӣеЎһе’ҢеҚўеҹәиҜәВ·з»ҙж–Ҝеә·и’ӮзӯүдәәйғҪжӣҫдёәиҝҷз§Қжҷ®йІҒж–Ҝзү№ејҸзҡ„еҸҷдәӢж–№ејҸиҖҢиӢҰиӢҰжҢЈжүҺпјҢеӣ дёәе®ғжҳҫ然дёҚйҖӮеҗҲиҲһеҸ°иЎЁжј”гҖӮдҪҶе…Ӣж—Ҙд»ҖжүҳеӨ«В·з“ҰйҮҢ科еӨ«ж–ҜеҹәйҖүжӢ©дәҶдёҖжқЎдёҚеҗҢзҡ„йҒ“и·ҜпјҢд»–еҜ№иҮӘе·ұйқ’е°‘е№ҙж—¶жңҹеҸ‘зҺ°зҡ„иҝҷйғЁдҪңе“ҒиҝӣиЎҢдәҶдёӘдәәеҢ–зҡ„йҮҚж–°иҜ йҮҠгҖӮ вҖңиҝҷжҳҜжҲ‘дёҺ马еЎһе°”В·жҷ®йІҒж–Ҝзү№дҪңе“Ғд№Ӣй—ҙзҡ„еҜ№иҜқпјҢдёҖдёӘеӨ–еӣҪдәәзҡ„и§Ҷи§’пјҢжҺўи®ЁиҝҷдҪҚжі•еӣҪж–ҮеӯҰеҸІдёҠжңҖе…·еҪұе“ҚеҠӣзҡ„дҪң家пјҢвҖқд»–и§ЈйҮҠйҒ“гҖӮиҝҷжҳҜдёҖз§ҚзӘҒз ҙеӣҪ家зәӘеҝөзў‘ж–ҮеҢ–дј з»ҹзҡ„з ”з©¶и§Ҷи§’гҖӮвҖңеңЁжі•еӣҪпјҢжҲ‘们дёҚдјҡи°Ҳи®әзҠ№еӨӘиЈ”жҷ®йІҒж–Ҝзү№гҖӮеҗҢжҖ§жҒӢжҷ®йІҒж–Ҝзү№пјҢз—…жҖҒзҡ„жҷ®йІҒж–Ҝзү№пјҢеӨ„дәҺзӨҫдјҡиҫ№зјҳпјҢиў«йҡҗи—Ҹиө·жқҘгҖӮвҖқиҝҷдәӣйғҪжҳҜ第дёҖж¬Ўдё–з•ҢеӨ§жҲҳеҲқжңҹжҷ®йІҒж–Ҝзү№зҡ„з§Қз§Қйқўеҗ‘пјҢдёҺжҲ‘们еҪ“д»ҠзӨҫдјҡвҖ”вҖ”д»ҺеҗҢжҖ§е©ҡ姻еҲ°еӣҪж°‘йҳөзәҝзҡ„иғңеҲ©вҖ”вҖ”дә§з”ҹе…ұйёЈгҖӮ
иҝҷеңәйҮҚж–°иҜ йҮҠзҡ„жј”еҮәпјҢйҖ е°ұдәҶдёҖеңәеҰӮеҗҢжҷ®йІҒж–Ҝзү№дҪңе“ҒиҲ¬йқһеҮЎзҡ„зӣӣе®ҙпјҢи¶…иҝҮеӣӣдёӘеҚҠе°Ҹж—¶зҡ„жіўе…°иҜӯжј”еҮәпјҢй…Қжңүеӯ—幕пјҢдёӯй—ҙз©ҝжҸ’дёӨж¬Ўдёӯеңәдј‘жҒҜпјҢд»ҘеҸҠдј—еӨҡзІҫеҪ©зҡ„иҲһеҸ°жј”е‘ҳпјҢдҫӢеҰӮеңЁе®үеҰ®В·иҠізҷ»жү§еҜјзҡ„з”өеҪұгҖҠж— иҫңиҖ…гҖӢдёӯеҮәжј”зҡ„йҳҝеҠ еЎ”В·еёғжіҪе…ӢгҖӮиҝҷжӣҙжңүзҗҶз”ұи®©жҲ‘们иө¶зҙ§жҠўиҙӯдёӨеңәжј”еҮәд»…еү©зҡ„еҮ еј й—ЁзҘЁпјҒ
е…Ӣж—Ҙд»ҖжүҳеӨ«В·з“ҰйҮҢ科еӨ«ж–ҜеҹәжҺҘеҸ—дәҶжҲ‘们зҡ„йҮҮи®ҝ
дёҖдҪҚжіўе…°еҜјжј”еҰӮдҪ•зңӢеҫ…жҷ®йІҒж–Ҝзү№иҝҷйғЁжһҒе…·жі•еӣҪзү№иүІзҡ„дҪңе“Ғпјҹ
жҲ‘е№ҙиҪ»ж—¶пјҢеңЁе…ұдә§дё»д№үж—¶д»ЈиҜ»иҝҮжҷ®йІҒж–Ҝзү№зҡ„дҪңе“ҒпјҢжҲ‘еҸ‘зҺ°д»–зҡ„дҪңе“ҒйҰ–е…ҲжҸҸз»ҳдәҶдёҖдёӘ并йқһиҝ·еӨұпјҢиҖҢжҳҜдёҚеҸҜжҺҘиҝ‘зҡ„дё–з•ҢпјҢ并еёҰжңүе…¶еҶ…еңЁзҡ„йӯ…еҠӣгҖӮжҲ‘е’Ңе°ҸиҜҙзҡ„еҸҷиҝ°иҖ…дёҖж ·пјҢж·ұж·ұең°иў«еҘҘдёҪе®үеЁңВ·еҫ·В·зӣ–е°”иҠ’зү№жүҖеҗёеј•гҖӮеҰӮд»ҠпјҢжҲ‘еҜ№иҝҷйғЁе°ҸиҜҙзҡ„и§ЈиҜ»жңүжүҖдёҚеҗҢгҖӮжңҖи®©жҲ‘еҚ°иұЎж·ұеҲ»зҡ„жҳҜе®ғзҡ„жү№еҲӨжҖ§пјҢеҚіжҷ®йІҒж–Ҝзү№еҜ№еҪ“ж—¶дё‘й—»зҡ„ж•Ҹж„ҹпјҢдёҚе№ёзҡ„жҳҜпјҢиҝҷдәӣдё‘й—»дёҺжҲ‘们еҰӮд»Ҡзҡ„дё‘й—»е№¶ж— еӨӘеӨ§еҢәеҲ«гҖӮж Үеҝ—зқҖзҺ°д»ЈеҸҚзҠ№дё»д№үејҖз«Ҝзҡ„еҫ·йӣ·зҰҸж–ҜдәӢ件пјҢжһ„жҲҗдәҶиҝҷйғЁе°ҸиҜҙзҡ„ејҖз«ҜпјҢиҝҷйғЁе°ҸиҜҙжңҖз»Ҳд»Ҙ第дёҖж¬Ўдё–з•ҢеӨ§жҲҳиҖҢе‘Ҡз»ҲгҖӮжҷ®йІҒж–Ҝзү№жҳҜжһ„е»әдё–з•Ңжң«ж—Ҙж„ҸиұЎзҡ„дҪң家д№ӢдёҖгҖӮд»–жҠҠиҮӘе·ұйӮЈдёӘж—¶д»Јзҡ„е·ҙй»ҺжҜ”дҪңеәһиҙқеҸӨеҹҺпјҢйӮЈйҮҢзҡ„еұ…ж°‘жІүжәәдәҺиүәжңҜзҡ„жө®еҚҺд№ӢдёӯгҖӮд»–зӣҙйқўиҮӘе·ұзҡ„еҗҢжҖ§жҒӢеҖҫеҗ‘е’ҢзҠ№еӨӘиЎҖз»ҹгҖӮд»ҺиҝҷдёӘи§’еәҰжқҘзңӢпјҢжҷ®йІҒж–Ҝзү№иҜ»иҖ…зҡ„еӣҪзұҚеҜ№жҲ‘жқҘиҜҙ并дёҚйҮҚиҰҒгҖӮжҲ‘жңҖж„ҹе…ҙи¶Јзҡ„жҳҜд»–еҜ№зӨҫдјҡдё‘й—»зҡ„ж•Ҹж„ҹпјҢд»ҘеҸҠд»–еҜ№дёҚеҗҢзҫӨдҪ“е’ҢдёӘдҪ“иў«жҺ’ж–Ҙзҡ„ж•Ҹж„ҹгҖӮ
жҙӣиҘҝе’Ңз»ҙж–Ҝеә·и’ӮеңЁжҷ®йІҒж–Ҝзү№иә«дёҠеӨ§еҠЁе№ІжҲҲгҖӮжӮЁжҳҜеҗҰйңҖиҰҒжңүзӮ№з–ҜзӢӮпјҢ并且дёҺеҪјеҫ—В·еёғйІҒе…Ӣиҝҷж ·зҡ„дәәеҗҲдҪңпјҢжүҚж•ўдәҺж’јеҠЁиҝҷеә§дё°зў‘пјҹ
ж”№зј–гҖҠиҝҪеҝҶдјјж°ҙе№ҙеҚҺгҖӢ并йқһз–ҜзӢӮпјҢиҖҢжҳҜдёҖйЎ№е®Ңе…Ёж— ж„Ҹд№үзҡ„иЎҢдёәгҖӮжҷ®йІҒж–Ҝзү№зҡ„е°ҸиҜҙжҳҜдёҖдёӘе®Ңе…ЁзӢ¬з«Ӣзҡ„ж–Үжң¬пјҢдёҖдёӘж— жі•ж”№зј–зҡ„ж–Үжң¬гҖӮеҪ“жҲ‘们йҳ…иҜ»е®ғж—¶пјҢжҲ‘们дјҡеңЁе…¶дёӯжүҫеҲ°иҮӘе·ұзҡ„и·Ҝеҫ„пјҢиҖҢдё”пјҢиҝҷдәӣи·Ҝеҫ„дјҡйҡҸзқҖдёҖж¬Ўйҳ…иҜ»е’ҢдёӢдёҖж¬Ўйҳ…иҜ»иҖҢдёҚж–ӯжј”еҸҳгҖӮжӯЈеӣ еҰӮжӯӨпјҢжҲ‘дёҚи®ӨдёәжҲ‘еҜ№иҝҷйғЁж–Үжң¬зҡ„еҲӣдҪңжҳҜж”№зј–пјҢиҖҢжӣҙеғҸжҳҜдёҖз§Қжҷ®йІҒж–Ҝзү№ејҸзҡ„иЈ…зҪ®пјҢз”ҡиҮіеҸҜд»ҘиҜҙжҳҜжҲ‘иҮӘе·ұеңЁе…¶дёӯзҡ„иЈ…зҪ®гҖӮиҮідәҺе°ҡжңӘе®ҢжҲҗзҡ„з”өеҪұйЎ№зӣ®пјҢжҲ‘иҜ»иҝҮз»ҙж–Ҝеә·и’Ӯзҡ„дёҖдәӣзҺ°жңүеү§жң¬пјҢжҲ‘ж·ұж„ҹйҒ—жҶҫд»–жІЎжңүж—¶й—ҙжӢҚж‘„иҝҷйғЁз”өеҪұгҖӮжҲ‘и®ӨдёәиҝҷйғЁз”өеҪұжң¬еҸҜд»Ҙдёәж–ҮеҢ–жҸҗдҫӣд»ӨдәәйҡҫеҝҳгҖҒиҝ‘д№Һж Үеҝ—жҖ§зҡ„еҪўиұЎпјҢи®©жҷ®йІҒж–Ҝзү№еңЁйӣҶдҪ“жғіиұЎдёӯеҸ‘жҢҘдҪңз”ЁгҖӮ
дҪ еҗ‘жҲ‘们еұ•зӨәзҡ„вҖңжі•еӣҪдәәвҖқжҳҜи°Ғпјҹ
еү§еҗҚдёӯзҡ„вҖңжі•еӣҪдәәвҖқжһ„жҲҗдәҶеҪ“д»Ҡ欧жҙІзҡ„вҖңж•ҙдҪ“вҖқпјҲpars pro totoпјүпјҢиҖҢ欧жҙІжӯЈз»ҸеҺҶзқҖиҮӘиә«зҡ„еҝ§йғҒгҖӮеҝ§йғҒжҳҜдёҖз§Қз–ҫз—…пјҢиҖҢз”ұжӯӨдә§з”ҹзҡ„жҮ’жғ°еҲҷжҳҜдёҖз§Қжү№еҲӨжҖ§жҖқиҖғзҡ„зјәеӨұгҖӮ欧жҙІзІҫиӢұ们жӯЈеңЁеҗһеҷ¬д»–们жҳ”ж—Ҙиҫүз…Ңзҡ„ж®ӢдҪҷгҖӮ欧зӣҹпјҢ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зҹҘиҜҶйЎ№зӣ®пјҢжӯЈеңЁеӨұиҙҘпјҢз”ҡиҮі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з»ҸжөҺйЎ№зӣ®пјҢд№ҹжӯЈеңЁеӨұиҙҘпјҢеӣ дёәе®ғжӯЈз»ҸеҺҶзқҖдёҖеңәж·ұеҲ»зҡ„еҚұжңәгҖӮжҲ‘们йғҪеғҸжҷ®йІҒж–Ҝзү№з¬”дёӢзҡ„дәәжҖ§дёҖж ·еӨұиҙҘгҖӮжҲ‘们еұ•зҺ°еҮәзү©з§ҚйҖҖеҢ–зҡ„зӣёеҗҢзү№еҫҒпјҢеҖҹз”Ёжҷ®йІҒж–Ҝзү№еҜ№жӨҚзү©еӯҰе’ҢеҠЁзү©еӯҰзҡ„еҒҸзҲұгҖӮжҲ‘们ж„ҹеҸ—еҲ°иЎ°иҗҪпјҢж„ҹеҸ—еҲ°з»Ҳз»“жң¬иә«гҖӮ